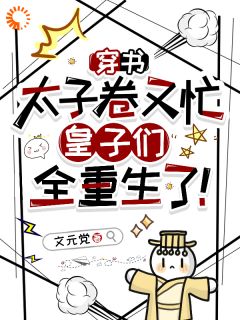
张奶娘这两日可谓春风得意,她本就是最得太子青眼的奶娘。
原先还有几个太监与她争权,太子一受伤,那些太监全没了。
进来的新人都得老老实实敬着她。
原先她中饱私囊还有顾忌,如今拿得理所当然。
太子饭食里面的门道多着呢。
太子人小一碗米糊糊几个青菜就打发了,但太子用膳的规格不小。
汤汤水水,干的稀的,加起来能点二十八道。
太子一定吃不完,她可以将没动的菜装起来送到宫外的珍馐阁,一道菜可以吃五两银子回扣。
于是大伤未愈的祁元祚就看到一桌子的珍馐美食……和奶娘手里的一碗蛋羹。
“殿下身子弱,桌子上的饭菜不养人,还是吃些蛋羹,好克化。”
张奶娘笑盈盈为他系上饭兜,喂他吃鸽子汤蒸蛋羹。
祁元祚皱眉看向张奶娘
“孤只有一碗蛋羹?”
“桌子上的菜不是给孤的?”
张奶娘哄道“当然是给太子殿下的,只是您肠胃弱,吃这些不消化,还是吃蛋羹。”
祁元祚继续发问:“这些菜是谁准备的?孤没有吩咐,为什么上了这么多菜?”
“孤不能吃,难道都扔了吗?”
张奶娘继续糊弄:“您是太子,您吃不完的当然是赏给下人,奴婢会帮您处理了。”
祁元祚表情冷了冷,只是圆润的奶膘拖后腿,只让人觉得他在撒娇。
这婆子都骑到他头上了。
他自然不会再留她,但是不该他来处置张奶娘。
他还是个宝宝儿,宝宝就该吃吃喝喝玩玩儿睡睡。
蛋羹很小一碗,味道不错,但吃不饱。
奶娘喂完了他一小碗蛋羹,向屋里人命令道:
“将饭菜撤下去,全都出去,太子殿下要吃奶了。”
祁元祚眼皮子一跳。
他想起来了,他还没断奶呢。
当今陛下十六岁成亲,四年才有第一个孩子,中间又隔三年才有了太子,子息不易,哪个都是宝。
民间只要家里有钱,吃奶到十岁的都有,皇宫里的奶娘至少也会伺候皇子至六岁。
奶娘的命令承祚殿的下人一时迟疑,纷纷看向小太子。
齐帝将承祚殿的人换了两波,唯独没有动奶娘,因此奶娘就成了太子跟前分量最重的了。
“还等什么?难不成要老婆子解了衣裳给你看着?”
奶娘理所当然的鼓动道:
“太子殿下,这些刁奴就该敲打敲打,否则还想欺主呢!”
真正三岁的小孩观念还没建立,这时候一定就听话由奶娘做主了。
祁元祚摸着扁扁的肚子问:“你想如何?”
张奶娘立刻来了精神,这可是她向新人立威的好机会。
凶狠道:“应该让他们跪下扇耳光!”
祁元祚托着腮,浅浅的眉一皱,看起来很是为难
“可是孤觉得他们没错,孤才是太子。”
“你说好听点儿是孤的奶娘,其实你和他们一样是伺候孤的下人,他们凭什么听你的?”
张奶娘放声痛哭,假意抹泪道:
“太子殿下出生后吃的第一口奶就是老妇的!”
“老妇将殿下从嗷嗷待哺扶养至今,是看作亲生儿子一样对待!殿下这样说,实在伤了老妇的心啊!”
这一招她以前百试百灵,一边拿着帕子擦眼泪,一边偷觑。
却发现祁元祚眼睛根本没在她身上。
一道明黄龙袍在殿外显现,祁元祚眼睛一亮,兴奋的招手
“父皇!阿父!”
张奶娘一听脸色大变,一骨碌站起来让出主道。
齐帝一进承祚殿就看到窥窗爱子,至于一群撒树叶的下人,被他自动忽略。
齐帝心情大好,几步走进去抱起爱子将手伸进帽子里呼噜他圆滚滚的小脑袋。
嘴上唠叨个没完
“元祚想没想父皇?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?”
“长大了可不准挑食。”
“伤口疼了吗?可有按时喝药?药苦不苦,下人准备饴糖了没有?”
祁元祚黏着齐帝,各种撒娇像露了馅的汤圆,夹着嗓子喊父皇声音甜的粘糊,笑的小奶牙都呲呲外露。
偏偏齐帝最吃这一套,爱的他不知怎么疼宝贝儿子才好。
亲热完了,就该告状了。
张奶娘抢先站出来
“陛下,奴婢正要给太子殿下喂奶,可是殿里的奴才不听吩咐不肯出去,这要是饿着殿下如何是好。”
承祚殿的奴才一个个跪下喊冤。
齐帝微微皱眉,他看到一桌子过于丰盛的膳食
“这是祚儿点的?”
张奶娘伶牙俐嘴:“是御膳房的奴才不尽心,殿下伤还未好,怎么就送来这么一桌子的菜。”
张奶娘将自己的责任推的一干二净。
祁元祚黏黏糊糊的撒娇:
“父皇,奶娘说我是太子,这些菜吃不完她会赏给下人,但是这好浪费啊。”
“一桌子的菜,儿臣只能吃一小碗蛋羹,还没有吃饱。”
“奶娘说可以喝奶,但是儿臣长大了,不想吃奶了。”
最高明的告状是让别人不觉得你在告状。
怀里的娃娃软乎乎的蹭着齐帝,他隐约还能闻到咸鲜的蛋羹味道。
齐帝看向桌子上空着的碗。
很小一碗。
‘她会赏给下人’,越俎代庖,自以为主!
最让他生气的还是‘没吃饱’。
他也是皇子过来的,哪还不明白里面的门道。
有些奶娘为了让主子离不开自己,会强迫他们一直吃奶,又或者只给吃个半饱,不得不吃奶。
桌子上的饭菜,每一盘都完完整整,说里面没猫腻,说奶娘清白,狗都不信!
张奶娘还欲再辩解,齐帝已经给她定了罪,挥一挥手,立刻有御前的人将人捂嘴拖走了。
齐帝有意盖住了祁元祚的眼睛,直到人走远了,他才松开。
祁元祚故作惊讶:“咦~奶娘会隐身!”
齐帝哈哈大笑。
“桌子上的菜,承祚殿的人分了吧,这是太子的赏赐,再做一碗粥来。”
他叫了太医,进行每天的诊脉和上药。
齐帝有意的教导儿子道理。
“祚儿是太子,太子什么都能做,他们是奴婢,敢越过主子的奴婢,都是刁奴,对于刁奴,元祚不可手软,该罚就得罚,该打就得打。”
祁元祚好奇:“那怎么罚,怎么打呢?”
齐帝耐心的教导他驭下之道,说到口干舌燥也不嫌烦。
祁元祚听的认真,心想不愧是帝王啊,心比资本家黑多了。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