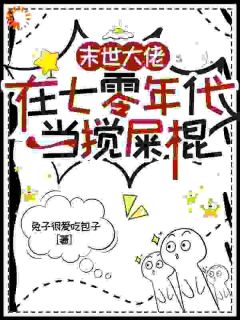第5章
天还没亮,时姝就已经醒了。
准确的说,是被身边的聂延秋给热醒了。
此时正值冬季,可聂延秋发热发得像个火炉,时姝赶紧起床打水来给他做物理降温。
时姝先用温水擦了擦聂延秋的脸部和手臂,不起效果后干脆全扒了,反复的擦洗大血管的经过处,末了还不忘一杯一杯的给聂延秋灌水喝。
大概擦了一个时辰,聂延秋身体滚烫的温度才稍微降了下来,而此时,天也蒙蒙亮,隐隐有曙光洒入房间。
时姝端着木盆去换水的功夫,床上躺着的聂延秋就从床上走了下来。时姝赶忙去扶住了他,“你腿上有伤,不方便行动。你想要什么,我帮你拿就行。”
聂延秋现在站起来,时姝才发现他个头很高。一米九几的个头,她站在他身边,又矮又胖,越发像武大郎。
终究是原主高攀了~
聂延秋甩开她扶着的手,“不用。”
时姝当然不依,再次扶了上去,“不用不好意思,既然你说给我三日时间,那这三日里,我便还是你媳妇儿。说吧,你要干什么?”
“如厕。”
“......”
由于时姝在迷迷糊糊间喂水的成功,一个时辰内,聂延秋硬生生跑了五趟厕所。
但好在,发热退了下来。
等天大亮,三个小不点也起了床。
时姝将昨日聂延秋发热后换下的衣服拿去湖边洗,正洗干净了打算回去,一个大石头却突然被人丢进了湖里,溅起的水花洒了时姝一身。
时姝回头,就看到几个男人包抄了过来。
“时妹妹,这两日过得可舒爽啊~”为首的男人肥头大耳的,叫她名字的时候油腻得很。
时姝认出这人就是赌场专门讨债的朱四。
朱四上次在聂家带走三宝不成,反被聂延秋给打了出来。聂延秋那厮居然还威胁他说要是敢再踏进聂家,就要卸了他两只腿。
当时迫于武力朱四不敢硬刚,但事后越想越气。正愁着该怎么教训一下聂家,就听说聂延秋在山上摔断了腿,于是他赶紧巴巴的带着几个弟兄又找过来了。
可巧,刚走到湖边,就看到了时姝自己一个人。
时姝望着靠近的人,向后退了两步。
刚穿过来事情太多,害得她都忘了,原主还有这么个麻烦没解决。
见时姝后退,朱四乐了,“哟,还知道害怕啊。前个躲在你男人身后,不是叫得挺凶的吗?”
“朱四爷,咱有话好好说。”时姝皮笑肉不笑,一双眼睛滴溜溜的转,想着该怎么脱身。
“我跟你可没什么好话说。既然逮不到小的,那就逮个老的回去交差。”
“朱四爷说笑呢,我长得丑,你抓我能干个啥?”
“长得漂亮的有长得漂亮的去处,长得丑,自然也有长得丑的去处。两个铜板一晚挂着,没人要就把你发卖去当军女支。”朱四说着,挥了挥手,“去,把时姝给老子绑了!”
马上,那几个打手就冲了上来,一把抓住了时姝。
眼见挣脱不开,时姝扯着嗓子大喊,“聂延秋,聂延秋快救我,聂......”
可这地方离聂家有些远,声音根本传不过去,更何况,她刚喊到一半,嘴就被人给捂上了。
眼看着就要被架走,时姝往家的方向看了一眼,没见到聂延秋出来,却看到大宝躲在草丛后,正望着自己。
时姝赶紧向他使眼色求救,可大宝像是没看到一般,转身跑开了!
完了!时姝的心凉了一截。
看得出来,三个小孩里面,大宝最不喜欢她,如今逮着机会,只怕是巴不得她越惨越好,哪里还会好心去告诉聂延秋来救她。
看样子,想要脱困,还得她自己想办法。
刚来洗衣服的时候,她有留意到旁边的芦苇丛里夹杂着几株紫红色的小草。这玩意儿有毒,但不致命,含在嘴里碾碎吐出来,会有一股浓郁的血腥味,就跟吐血了一样。
眼下,用这草蒙混过去,或许能有一线生机。
但她需要一个契机,吐血的契机。
望着走在最前面的朱四,时姝想起了他老婆跟人跑了的事情。据说朱四特别不喜欢别人提这件事,一提就会打人。
想到这里,时姝眯了一下眼,已是计上心来。
走到芦苇荡时,时姝突然拽住了树干不撒手。她吨位重,此时发难,那几个大汉居然一时间还拽不动她。没法子,那个捂住她嘴的大汉只好先挪开,去掰时姝的手指。
得了机会,时姝就开始戳朱四的短处骂。刚骂了两句,朱四就一个巴掌甩了过来,“你找死!”
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一下,时姝整个人都被煽到芦苇丛里,眼看着朱四还要走过来打人,她赶紧在倒下去的瞬间抓了一把紫红色的草塞进嘴里。朱四的下一巴掌还没打过来,时姝已经口吐鲜血,全身抽搐起来。
“这什么情况?”朱四后退了两步,惊恐的与打手对望了两眼,“我手劲也没这么大啊!”
“四爷,我看她这模样,像是撞到脑袋了。不会死人吧!”
“瞎说什么呢?”朱四瞪了他一眼,望着地上血越吐越多的时姝,有些慌神。
杀人可是犯法的,这要是被人撞见,他就是有几张嘴也说不清。
朱四四下望了一眼,见周围没人,跺了下脚,“真他娘的晦气,赶紧走,谁都不要说今天我们来过这里!”
听着朱四几人的动静远去,时姝装抽搐的动作才停了下来,从芦苇丛里站起身。
她走过去,将丢在湖边的木盆和衣服收拾好,才慢悠悠地往家的方向走。
彼时,聂延秋将一截树枝削成了拐杖,拄着在院子里试了一圈,发现末端有些不平整,便让大宝去拿柴刀过来,可喊了三遍大宝才听见。
大宝的反常让聂延秋心里奇怪,于是随口问了一句,“大宝,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?”
“没有。”大宝的头摇得像拨浪鼓。可越是回答迅速,越是可疑。
“你是不是刚才出门看见了什么?”
“啊......我,我什么都没看见。”
“真的?”聂延秋抿紧了唇,“我是不是说过,我的儿子,可以胆小,但不能害人。”